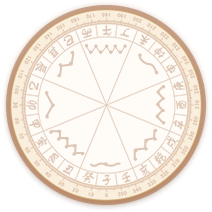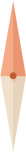2022年12月21日,是上海博物馆开馆70周年的日子,70年来,这座博物馆与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经历了怎样的融合与互动,博物馆在保护和传承城市文化中有着怎样的责任担当?上博这座文化地标,在展现城市文化积淀、打响城市文化品牌、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一座博物馆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见证和讲述着历史,更在于它为未来社会提供了无限想象空间。
在上博70周年之际,澎湃新闻推出“爱上博物馆”专题,讲述“博物馆与大都市”、“博物馆与都市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见证历史,望见未来。
上海博物馆考古部原主任宋建
上海博物馆考古学的学术地位一直以来在国内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命名了崧泽在内的多个考古学文化,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文明探源预研究第一次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地。近期,上博主导的长江口二号水下考古,再次引起考古界关注。
宋建在上博考古部工作多年,从1987年来到上博工作,到2015年办理退休,从助理研究馆员、副研究馆员一直做到研究馆员和考古部主任。当年如何从开发商手中“抢”到几块重要遗址?考古工作对专业人士和大众各有怎样的意义?未来上海的考古工作应该怎样发展?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宋建分享了他的考古故事和专业思考。
澎湃新闻:上海曾一度被认为“无古可考”,您觉得上海博物馆的考古工作分为哪几个发展阶段,有什么标志性的事件?
宋建:上海博物馆建馆以后,考古工作开展主要有几个大的时间节点。第一个节点是1958年,这个时候,上海地域第一次扩大到了现在的郊区范围。在此之前,上海仅仅是现在的市区范围,还没充分条件开展比较有深度的田野考古。地域扩大后,马上开展了各种调查发掘,现在很有名的遗址,比如马桥、崧泽、广富林,都是在1958至1961年间首次发现的。没有从事田野考古的客观条件,也不会有后来的考古成就。
第二个时间节点就是1960年代初,青浦崧泽遗址的发掘。后来崧泽文化的命名就是以崧泽遗址的发掘为基础,自此上海有了第一个考古学文化命名的遗址。
第三个时间节点是1982年,青浦福泉山的首次发掘。此后的多次发掘证明,这里发现了一个良渚文化5000年的文明古国。相当一段时期以来被认为是汉代甚至更晚的玉器,由于福泉山等地的发掘,一下子把年代提早了几千年,并且福泉山第一次发现了清晰可考的地层关系,为良渚文化的分期提供了准确依据。
第四个时间节点是1990年代初,马桥的发掘,大大拓展了马桥遗址的分布范围与规模。
第五个时间节点就是本世纪初,以古代城镇的起源和发展为课题,开始了青龙镇遗址的大规模发掘。
归纳起来,大概就是以几个重要意义的发掘为串联,因为每个重要遗址的发现,都是和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相关联的。
澎湃新闻:在这么多的考古项目中,您参与过其中的哪些项目?
宋建:这其中很多考古项目我都参与过,但是印象最深的,参与全过程的,还是马桥遗址的发掘。马桥是我学习阶段最关心的题目,我最早的学术论文,就是关于马桥文化的。当然最初是纸上谈兵,到了上海以后,发现自己有条件从事马桥的发掘了,就着手准备起来了。我刚来上海时跟在别人后面干;后面我担任领导了,又是指导别人如何干,马桥是我作为考古研究人员独立主持又全过程参与的一个工地,是我最上心、最全身心投入的项目。
澎湃新闻:马桥文化本来是一个不大的遗址,后来您是通过怎样的努力,让它成为了重要的文化遗址?
宋建:大家对马桥可能不太重视,因为它不像良渚那么丰富,在全国那么有地位,学术意义那么大。同时它也不像崧泽那些遗址,在新石器时代的年份比较早。马桥是夏代和商代的,我们知道,夏商中国的文化中心并不在这块地区,环太湖地区那些先进的文化要素很多都已经传播到其他地域,包括中原地区了。所以马桥在全国来说并不是很有名。我挑选它,也是有一份前面说的初心在。
当时一些老先生对我说,马桥遗址不大,只有五千多平方米,在1960年代的时候已经发掘完了,我当时也表示,先去试试看。之前马桥遗址主要在北松公路南面挖,我就在北面选了一个点开始挖。
当时我们发掘的时候,边上有人在挖沟,于是就过去看,他们说他们这里要挖一个墙基槽。他们对我们挖的东西也感兴趣,我给他看了以后,他说这个不稀奇,再往北过去一两百米有很多。我还不太相信,如果这个距离属实,就已经要将遗址面积扩大几万平方米了,然而我跟着他的指引到了北边,一看,确实是大批马桥文化的遗物。当时这个地块已经批租给了香港的一个房地产开发商,准备搞建设了,我马上取证,然后和他们交涉,要他们停工,并向上汇报。
这次的发现让马桥遗址从原本5000平方米扩大到15万平方米,扩大了30 倍。这样就对马桥文化当时先人的生产生活活动有了更多的发掘空间,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研究材料,更多的解释余地,更多的新结论。
澎湃新闻:您在上博考古部工作中,获得过来自上博的哪些支持?
宋建:上博在1980年代、1990年代的几任主要领导,都是当时国内的顶级专家。当时的馆长马承源,对外主要身份是青铜器专家,但是他是中国考古学会的理事,对青铜器精通得很多。虽然他不亲自参与田野发掘,但他利用考古田野发掘的出土品,从事考古研究,给仰韶的彩陶写过一本小册子。副馆长黄宣佩,他更是直接从事考古工作,那些重要遗址,广富林、崧泽、马桥、福泉山都是他做领导时发现的。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考古的内行人,所以他们对考古工作非常支持,非常理解。
就像刚刚说到的马桥,当时碰到困难的时候,我首先就搬出黄馆长,因为他分管这块。我把他带到工地,跟他说,马桥比你想的5000平方米要多多了。他知道这是一件大事,但这件事光他也还不够,于是我又去请马承源馆长,马先生当时是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
情况很复杂,外资当时是稀客,又是通过合法途径取得的土地,所以中间的交涉非常艰难,二位馆长都出了很多力。当时的上海市副市长龚学平也很关心考古工作,最后他做了批示,有了市里指示,和地方上打交道容易多了,也最终成就了马桥范围扩大30倍的重大成果。
还有一个馆长我也不能漏掉,就是本世纪初分管我们的汪庆正副馆长。当时有了志丹苑水闸遗址的线索,我拿到文管委工作例会上汇报讨论,受到一些质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不是古代的,可能是日本人留下的防空洞,或者是地下碉堡。汪馆长主持这次会议,他给我提了个要求,他说现在的争议是很大,因为那个地方要开发房地产,你让人家停工,政府出了钱以后,结果你挖出一个日本人的碉堡,我们上博脸上肯定挂不住。他说我给你七天时间,你去做个调查,第一,去看看这是什么性质的遗存?第二,确定一下大致的年代,把这两点搞清楚,我就支持你。我跟他讨价还价了一下,我说再给我增加三天,十天时间保证完成,完成不了就不跟人家争了。后来,我就大致鉴定出这是水工遗址,属于宋元时期。汪馆长就拿着这个证据去上海市政府汇报,讲得也很生动有趣,把当时与会的市长、副市长讲得频频点头,结果,会上就当场拍板了。可以说上博的领导给我们的支持力度是非常大的。
上博的其他部门也给了我们很大支持。比方说,我们考古部门的修复力量是不够的,我们出土的瓷器陶器、金属器、漆器等都交给文保中心来修复保护。因为有上博领导的支持,还有各个部门之间的通力协作,也是我们考古部门能够取得这样大成就的基础。
澎湃新闻:亲自挖掘的文物中,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
宋建:我挖掘出的东西很多,就举几件有代表性的器物,比如象牙权杖,考古部有多名工作人员参与发掘,我在现场发掘指导。象牙权杖不是第一次发现,第一次是在浙江反山20号墓,他们判断这个东西是象牙器,但是那上面没有发现花纹、神像。虽然早就发现,但是没有准确认识。
现在,距离福泉山那件象牙权杖出土已经十多年了,目前也仍然是唯一保存如此完好的象牙权杖,上面有十个清晰的良渚文化神像图案。刚挖出来的时候,凭借我对花纹的敏锐,一下子就意识到这是良渚文化的神像图案。我们当时也非常重视,把墓葬整体运到室内进行清理。
另外一件就是马桥报告那本书封面上的鸭形壶。它不像绝大多数陶器、铜器是对称型的,它是非对称型的。鸭形壶在马桥文化里本身就非常少,更奇妙的是,绝大多数鸭形壶都是用红褐陶,或者硬陶做的,而这件是用泥质陶做的。陶质虽然不硬,但纹饰可以更加精细,是云雷纹。这是马桥的一件典型器物,我也很喜欢它,就将它放在马桥报告的封面上。而在夏文化的二里头,也发现了一些鸭形壶,多数研究者认为是南方制作完运到了北方,鸭形壶也被认为是研究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器物。
澎湃新闻:考古工作对于您和大众而言,都有怎样的意义?
宋建:就像人到了一定年龄阶段会回忆他的过去,人类其实到了一定阶段,也会去想我们的过去是怎样的,未来会到哪里去。我们中国其实有一套非常完整的文字系统来记录我们的历史文化,和其他文明有中断不同,我们的文明是很连贯的。但是经史子集这些书籍,主要是记载王侯将相的事情,经济、科技等方面介绍得就有限。所以最初考古的想法是为了能够补充文字中没有记载的部分,就是所谓的“证经补史”,证明“经”的正确性,弥补史书的不足。
当然,这个提法肯定是有局限性的,我们现在的考古,已经不仅仅是“补”,更多是一个重建历史的问题,文献上没有记载的,或者是传说的,就要用考古来建立一个古代史。
作为大众,他可以通过考古了解一下中国古人是怎么生活生产的,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他们生活生产的方式,除了对我们现在文化生活是一个补充,也是对我们知识的补充,让我们思考如何在今天更好地生产和生活。
澎湃新闻:这些遗址所反映的生活与生产经验,能给我们今天怎样的借鉴?
宋建:我觉得其一是人居和自然环境的和谐。我就举马桥的例子,它和很多遗址分布不一样,不是一个长宽大致相当的城镇,它的南北长1000多米,东西才100多米,和当时很多城镇、聚落不相符。为什么?很简单,就是和当时环境有关。当时自然环境就是一道很长的沙堤,东边是海洋、滩涂;西边是湖泊、沼泽、森林、草原,地势都比较低,就要选择在一个高亢的地方生活,既避水又近水——可以通过水获得很多的生活资源,但是又不会受到水患的影响。这就是很典型的人居与环境共生共存。如果别处说是上海的文明之源、城镇之根,那么马桥所在的闵行就是上海人居之本。
其二就是人和水的关系,人是逐水而居的。最早青龙镇是上海的中心,因为当时航运也好、捕捞也好,工作生活都是沿着吴淞江。它被黄浦江取代以后,中心就到了现在的上海老城厢。这就是水在城镇迁徙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河流,它是我们人类生存的一个根基。
澎湃新闻:考古是小众的还是大众的?博物馆与考古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宋建:其实它既是小众的,又是大众的。考古很多的研究题目是一门科学,需要一批直接和这个专业相关的人去进行一些高层的、顶端的研究,而且目前也有很多新的技术,不可能社会大众都来进行研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个小众的东西。
同时,它的成果是要大众化的,要把成果转化为让大众了解的知识、常识,我们对于种种现象不用了解得很深,但是要了解,我们的社会、经济、文化是怎样一步步发展过来的。
而要让这些小众的知识变为大众的常识,博物馆是一个很好的场所和媒介,很多科普就是在博物馆中发生的。博物馆现在也成为城市的一张名片,是去观察这一地区、这一族群很好的窗口,也是乡土教育的一个重要基地。
澎湃新闻:是什么支持您在考古事业中坚持了这么多年?
宋建:考古行业,我们那个时候可能还非常冷门,但现在不太一样了。像我们现在考古部有几位年轻的女孩子,我说你怎么会选择学考古的?她说也很简单,小时候看了夺宝电影,然后产生了兴趣。当然了,真的选择这个行业,就会发现和夺宝肯定有区别。我们那个年代去野外,常常会去一些人烟稀少、荒芜的地方。到了冬天,冰天雪地,早上地面全冻住了,要等到太阳出来以后慢慢化了,才能开工,而且还不能太烂,还要等它稍微干爽一点。夏天室外又会非常热,三十七八度,甚至四十度也是常有的事情。
这个行业也能寻得很多乐趣。在发掘工作中,有很多未知,一趴一蹲,一连几个小时,但是,你一旦挖到东西就非常兴奋。考古工作让人有一种期待,这样挖下去,我可以看到什么东西,可能会获得什么。
无论你从事哪门学科,都有它艰苦的、枯燥的地方,但同时它也有它的引人入胜、令人产生兴趣的地方,关键就是要投入、认真、用心。慢慢坚持下来以后,你会觉得你做了很多有意义的事情,时间也真的过得很快。
澎湃新闻:您对未来的考古工作有怎样的建议和期许?
宋建:概括地说,首先要面向全球,这要求我们不光站在上海看上海,而要跳出上海看上海,就是要有全国视野、全球视野。我们工作目标还是上海,帮助上海重建它的古代史。因为记载中的上海历史非常简单,要到春秋战国以后,夏商都是没有的,更不用说新石器时代。
那么重建上海历史的路径是什么?一个是文明的进程,就是上海古代文明的进程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的。比如说福泉山,我们把它放到整个良渚文明时代观察,发现它在整个良渚千年过程中,它在后500年有异军突起的势头,就包括象牙权杖,所以这也值得我们考古人仔细研究,讲好这后500年的故事。
另一个就是城镇的起源和发展,这也是世界上考古工作关注的三个起源之一。我们上海的代表地点就是青龙镇。华亭县等地因为反复拆建,原貌已经看不到了,而青龙镇随着吴淞江的地位降低以后,很快就湮没了,埋藏在1米深的地下,保持了非常好的唐宋时期城镇面貌,给了我们很好的研究契机。
我们在2014年做过一次上海的考古大展。当时一共是三个题目,其中就有“文明之光”和“城镇之路”。这两个题目很大,不仅仅只是做个一年两年,甚至都不是几十年,将来很长时间的考古工作都将围绕两个题目来展开。
 人人都是经理人,人人都是财务经理人-管理知识分享,财务知识分享,会计考试知识分享,经济师考试知识分享,职业经理人互联互通平台!
人人都是经理人,人人都是财务经理人-管理知识分享,财务知识分享,会计考试知识分享,经济师考试知识分享,职业经理人互联互通平台!